艺苑论剑|电影《大风杀》:风沙中的博弈
犯罪悬疑电影《大风杀》凭借其暴力美学的视听呈现、独特的西部风格以及深刻的人性探讨引发了广泛热议,然而,从类型片的角度审视,影片在形式与内容上存在明显的割裂。创作者过度追求视觉效果和隐喻意象,使得叙事逻辑显得混乱,角色塑造趋于符号化。这些问题不仅削弱了影片的叙事连贯性,也让观众难以深入共情。而这种困境,恰恰也是当下许多国产类型片亟待突破的瓶颈。


人性迷思与生命叩问
文|孙瑞
漫天的风沙,枪声肆虐,边陲小镇的风沙里正上演着一场关于人性的博弈。由张琪执导的《大风杀》,在西部片的荒凉萧瑟之下是对人生本质的叩问。警察与悍匪的枪口对峙,不过是表象的戏剧冲突,真正的困局,是每个人在“我是谁”“我从哪里来”“我要到哪里去”的叩问中被孤独与迷茫吞噬的挣扎。
从视觉层面看,影片极具西部片的视觉化元素。遮天蔽日的黄沙,破败不堪的村落,锈迹斑斑的招牌在风中摇曳,无不透露着边陲小镇的萧瑟与荒芜。影片开始,如同汹涌潮水般肆虐的黄沙铺天盖地般袭来。猛烈的风沙暂未停歇,血腥的悍匪又涌入小镇。街道上的机枪扫射,屋顶上的狙击猎杀,子弹如雨点般倾泻。

白客饰演的夏然一角,虽然果敢、勇猛,但也有面对悍匪拿枪时的颤抖与惶恐,在力量悬殊的困境下,他能做的也只有等待和避免与悍匪产生强烈冲突。对于警察简宁的塑造,完整地呈现了人物弧光。从羊圈戏中的畏畏缩缩,因失误开手电筒间接造成了罗小杰的死亡,到后来能独当一面,完成了从脆弱、懦弱到坚韧的成长转变。对警察老罗的塑造,主要体现在废旧泳池一场戏中,他以性命为代价,用话语戳中赵北山的痛点,只为给夏然争取时间,而置自己的生死于不顾。影片不仅注重雕刻单个人物的成长轨迹,更勾勒出一幅警察的群像。角色在褪去光环后,更显人性的复杂与真实。
影片《大风杀》英文名为“Trapped”,意为“受困的、陷入困境的”。这种困局看似是在有限的小镇空间中警察与悍匪陷入对峙的困局,实则隐喻着人们心中共同的精神困境。小镇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从何处来的迷茫以及向何处去的困惑。

片中赵北山和夏然的对话片段具有哲学意味。赵北山坦言:“我不在乎钱,也不在乎命。”“那你在乎什么?”夏然追问。赵北山回答:“我不知道啊夏警官。我甚至不在乎我知不知道。”
赵北山是影片中最大的反派,他在监狱被关押三年后,面临着手下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,他的孤独源自于害怕被人抛弃,所以赵北山被空虚所吞噬。他通过不断地杀人来维系自己扭曲的“尊严”和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——就像罗警官在死前的一番话道出了他自卑的本质。他越执着于别人对他的绝对服从,就越暴露出他的自卑以及内心的荒芜。
白客扮演的警察夏然是一个独行兵,不需要队友、不需要伙伴也不需要战友。影片伊始,夏然的独白便奠定了其孤独的基调:“他们都管我叫夜猫子、猫头鹰、报丧鸟,报死人信的。”影片最后,他为了抓捕悍匪,孤身一人骑着摩托,踏上了追凶之路,尽管前方风沙弥漫,却一往无前。正如他对简宁所说的那样:“永远往前看!不要回头看!”
片中夏然与赵北山两人互为镜像,都面临着来去的茫然。两人虽身处不同的境地,却都在自我认知的困境中苦苦挣扎,孤独成为他们共同的底色。当漫天的风沙停止,影片给观众留下的不仅是鲜血喷涌、机枪杀戮所带来的暴力感官刺激,更是对人生命本质的叩问。
(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)

形式与内容的割裂表达
文|王文轩
《大风杀》以其暴力美学的视听呈现、西部风光的场景营造和精湛的人物演技,吸引了众多观众去影院一探究竟。然而,当观众走出影院时,评价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,有的观众震撼于导演对于叙事节奏的独到把控,有的观众失望于影片叙事逻辑的不能自洽。这些问题,也折射出当下国产类型片的部分困境——当创作者沉溺于形式上的美学狂欢时,失控的内容表达与涣散的主题让电影沦为被风沙侵蚀的“空中楼阁”,徒留一副空壳。
《大风杀》对形式感与沉浸感的追求堪称极致,风沙下的边陲小镇以及正义警察与狂暴歹徒的设定,复刻了经典西部片的类型范式。导演对灯光、音响和视觉符号的过度使用,更是让电影时时处处都笼罩在紧张悬疑的氛围当中。影片开场便奠定了电影“浓厚”的黑色气质,一处废弃的加油站被肆虐的荒漠风沙所覆盖,密闭的空间下,每个人似乎都心事重重,表现主义风格的灯光设计让画面平添些许恐怖氛围,刺耳的音效配合铁丝捆人的特写镜头带来视听冲击,枪响后的静默成功构建出蛮荒场域的末日氛围。电影用长达近20分钟的画面以及声音设计,只是为了交代劫匪老大的成功越狱,形式与叙事的严重失衡,让观众无法在众多画面中获取有效信息,也渐渐失去了戏剧张力。

这种失衡在影片后半部分更加明显,一边是内部秩序早已土崩瓦解的匪徒帮派,“黑吃黑”的戏码频频上演,它脱离叙事主线甚至占据了大量篇幅,杀与被杀的动机也十分牵强,似乎只是为了呈现枪战和小团体之争的血腥场面;另一边是三名代表正义的警察,案情发生之后,他们一直与匪徒暗中斡旋。而最后冲突的消解都化归于沙尘暴的来临,风沙作为外在表象在电影中得到了超乎神化的处理,彻底摒弃了现实主义的深刻叩问。这种形式符号的过度使用,使得前期精心铺设的悬疑氛围与人性拷问最终沦为一场视觉狂欢。
影片想要通过群像叙事表达人性命题,却因形式感的营造让角色塑造陷入符号化的窘境。辛柏青饰演的匪首北山是相对立体的存在,他既癫狂又优雅,既痛恨背叛又害怕孤独,这样一个割裂矛盾的个体,在电影中,只成为发动恐怖行动的工具符号,导演仅仅赋予了他“我不在乎钱,也不在乎命”的虚无台词,并没有体现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和根源。北山只是作为一个反派存在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。其他角色则更加单薄扁平,影片唯一的女性角色李红,只是作为为妹妹复仇的姐姐而存在,她与妹妹之间的情感简化为几句苍白无力的台词,这让观众难以信服她与妹妹之间的深厚情感,她拉响炸药和杀害妹妹的凶手同归于尽的行为,更像是导演设置好的剧情开关,而非角色情感积累的必然。夏警官的徒弟简宁因夜盲症而误杀好人,本可成为探讨道德困境的切入点,却沦为使他强行成长的工具事件。还有匪帮内部的众多角色如会计、曲马多和舌头等,因为背景交代不足,导致他们的存在与死亡都显得非常突兀,本可以用这场杀戮深究人性之恶,最后却沦为刻意打造暴力美学效果的视觉工具。

隐喻意象的泛滥致使主题表达贪多求全,让电影陷入“多义性”局面。“风沙”意象的运用贯穿全片,风沙下的人物也具有隐喻色彩,反派北山所建立的江湖秩序与另一帮悍匪的功利主义形成对立。夏然腿脚不好,奔跑时会产生生理性疼痛,这其实是战争带给他创伤的外显呈现,最后将北山擒拿归案也代表着夏然战胜了自己,拨开了阴霾,个体实现自我救赎。意象的使用本可以映射寓言,但当每个意象都有隐喻时,反而会导致内核涣散,削弱了核心命题的穿透力,造成观众在理解上的困难,使得主题只是概念化的阐释而并没有深刻的思想深度。
(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2024级研究生)

(责任编辑:admin)
下一篇:没有了


 周杰伦晒昆凌与小女儿合照
周杰伦晒昆凌与小女儿合照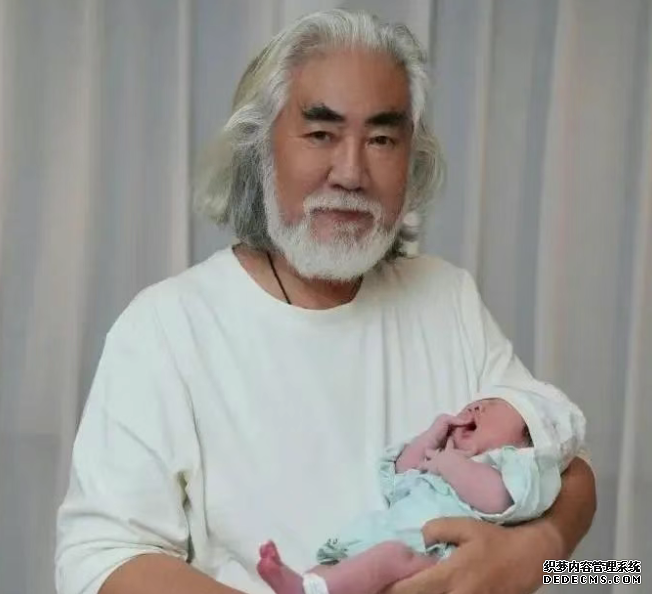 汪明荃多大年龄了?78岁汪
汪明荃多大年龄了?78岁汪 章泽天刘强东婚姻命理般配
章泽天刘强东婚姻命理般配 陈晓旭出家图片 原因是什
陈晓旭出家图片 原因是什 大S去世后小S首发文 说大S
大S去世后小S首发文 说大S 孙俪发文告别新剧并感谢老
孙俪发文告别新剧并感谢老 尹恩惠为什么突然
尹恩惠为什么突然 人到中年,我终于
人到中年,我终于 易烊千玺独家演唱
易烊千玺独家演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