杀死一个人渣,然后呢?(2)
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·特克在《群体性孤独》(台译本为《在一起孤独》)一书中集中讲述了科技时代人类社会的种种病症,在对400多名受访者进行走访调查之后,雪莉指出当代社会正在逐渐形成「一种表演性文化」,社交媒体似乎营造了人际更好的沟通,其实这是错觉,实际上却让人们更加孤立。一方面人类在网络上重新塑造自我,另一方面,这种塑造中「叙述性和分析性的思考越来越少见」。 人们用字母代替话语,用表情符号替代感觉,点亮一个竖起或向下的拇指就能代表赞同和反对,心理状态逐渐形成一种惯性的表演机制,科技的进步让这类表演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。
理清了表演性文化下这种群体性的孤独和群体性的残忍,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在此基础之上试图营造一个对话的空间——律师王赦一直像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一样,争取大家能平静下来,能想一想为什么。这也是整部电视剧的核心命题:在无解的悲剧面前,在科技便捷到今天的当下,人类还是否拥有对话和自救的能力——我们能不能在网上的义愤填膺之外,喊打喊杀之外,没完没了地标签化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之外,仍旧有静下心来的勇气,能跳出自身的偏见和仇恨,让一起绝望心碎的悲剧事件,能够拥有「杀死一个人渣」之外,一个不同的结局。

剧中为「恶人」辩护的法扶律师王赦致力于了解犯罪者背后的原因,以避免未来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图源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
「全天下没有任何一个爸爸妈妈,要花一个二十年,去养一个杀人犯。」
整部剧中最刺痛人心的,是凶手的妈妈哭着喊出的这个句子。关于剧中李晓明为什么会枪杀那么多无辜的人,电视剧始终没有给出答案。但是剧中安排了一条患思觉失调症(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精神分裂症)导演的支线,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导演,一路遭遇资本的摧残、众人的嘲笑、家人的不解,然后在病发的时刻成为一则社会新闻的男主角,在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后,迎接他的世界并没有多少同情和理解,而是接连的排斥和恐惧,他被永远地当成一个病人。

患上思觉失调症,无比痛苦的青年导演应思聪图源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
他的故事大约能解答部分杀人犯从何而来的疑问,身处一个充满戾气和缺乏理解的社会,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,都觉得命运讽刺和不公,但极少有人意识到,自己的偏见和恐慌,甚至一个眼神或社交媒体上无意的一个赞同或反对,可能都在无形中制造了我们身边的「恶」,我们一边咒骂,一边身为凶手而不自知。
「思觉失调症」的案例取自三年前发生在台湾的「小灯泡」事件,2016年,四岁女童小灯泡在骑脚踏车前往捷运站途中被一男子砍杀,小灯泡随即身首异处,后经警方调查,行凶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。他与小灯泡素不相识,因为案件性质恶劣,当时全岛一片喊杀之声,让外界讶异的是,目睹事件经过、几度崩溃的小灯泡妈妈,在之后的社交媒体上和接受媒体访问时多次提出,与其满足民意去杀死一个人,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。这位母亲的克制和隐忍一度让外界错愕,甚至有不怀好意的人对她进行攻击,但这位妈妈说,小灯泡是个在爱中长大的孩子,当离开成为事实,这位妈妈希望这起不幸的事件能够引发整个社会的思考,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改变。

「小灯泡」事件,左为罪犯右为受害者家庭图源网络
一百多年前,法国作家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中给了冉·阿让一张黄色身份证,让他成为永远的下等人和苦役犯。它是冉·阿让永远的标签,也凝结着那个世界中洗脱不掉的审判和偏见。如果没有遇到米利埃主教,拿着黄色身份证的冉·阿让,大约会被那个世界逼成可耻的窃贼和暴徒。
世界飞速进步的同时,人性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原地转圈,今天我们生存的世界并没有比冉·阿让的世界更好一些,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中给出的答案是宽恕和同情。在这个刻薄的年代,面对汹涌的愤怒和仇恨,宽恕和同情永远是稀缺品,它们当然不会让愤怒或是仇恨消失,但正是因为这些品质的存在,我们的世界才不至于真的崩塌。
大约还是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中概括的最为精确,「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,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,光明和黑暗交织着,厮杀着,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。」
(责任编辑:admin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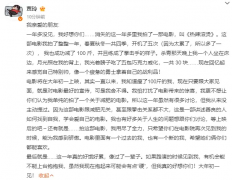 贾玲成功减肥100斤 新片《
贾玲成功减肥100斤 新片《 郭富城担任领克汽车品牌大
郭富城担任领克汽车品牌大 《繁花》让黄河路人多到新
《繁花》让黄河路人多到新 2024山东春晚阵容官宣 山
2024山东春晚阵容官宣 山 《三体》剧集预告片发布
《三体》剧集预告片发布  檀健次代言滴滴出行 滴滴
檀健次代言滴滴出行 滴滴 尹恩惠为什么突然
尹恩惠为什么突然 人到中年,我终于
人到中年,我终于 易烊千玺独家演唱
易烊千玺独家演唱